論世界版權公約中“向公眾提供權”的含義
內容提要:網絡深層鏈接是否屬于向公眾提供,在理論界與實務界存有較大爭議。在國內,有“服務器標準”與“實質呈現標準”的對立;在歐盟,有“新公眾標準”與“特殊技術手段標準”之爭。通過應用法律解釋學的方法,對國際版權公約規定的“向公眾提供權”進行充分闡釋,提出“間接提供理論”,即“向公眾提供權”既包括向公眾直接提供的行為,也包括向公眾間接提供的行為,后者可以作為規制深層鏈接的理論依據。
關 鍵 詞:國際版權公約;世界版權公約;向公眾提供權;深層鏈接;間接提供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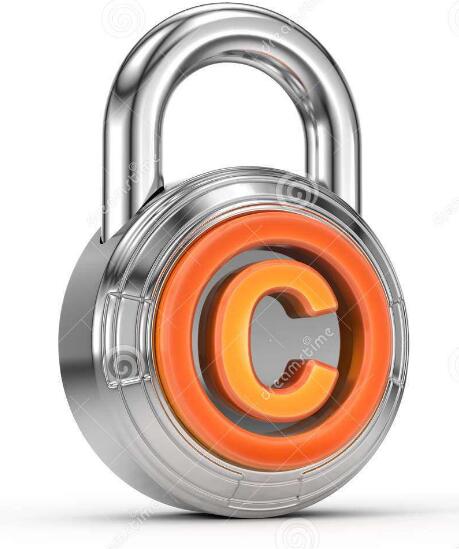
一、向公眾提供權的含義
(一)《維也納條約法公約》
根據《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的規定,任何條約首先應“依其用語的通常意義”進行解釋(文義解釋方法);用語的通常意義應根據它們出現的上下文進行解釋(系統解釋方法)。要確定條約約文的含義,除了要考慮上下文的含義以外,還要考慮條約的目的和宗旨(目的解釋方法)。如果依前述解釋方法進行解釋而“意義仍屬不明或難解,則可以使用解釋之補充資料,包括條約之準備工作及締約之情況”(補充性解釋方法)。
(二)向公眾提供權的條約法解釋
1.文義解釋方法
從文義解釋來看,“make (making)available to the public”的含義是:使一般普通民眾可以獲得。從這一解釋來看,“提供”一詞的含義是非常廣泛的,而且也是技術中立的。事實上,也正是由于這一原因,WCT才選擇將提供權作為適用交互式傳輸的權利類型;對此,下面將詳細論述。
2.系統解釋方法
從上下文來看,在WCT中,由于第8條(“向公眾傳播的權利”)使用的措辭是:“……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應享有專有權,以授權將其作品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包括將其作品向公眾提供,使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可獲得這些作品。”
因此,一般認為,在WCT中,提供權屬于向公眾傳播權的子權利。但是,在WPPT中,提供權則是作為單獨的條款來規定的:WPPT第10條“提供已錄制表演的權利”和第14條“提供錄音制品的權利”。也就是說,在WPPT中,“向公眾傳播”并不包括WPPT第10條和第14條規定的“提供”表演和錄音制品的行為。
正如下所述,WCT與WPPT采用的是“傘形解決方案”;締約國在國內法實施國際公約義務,規制交互式傳輸行為時,可以采用作為向公眾傳播權子權利的提供權模式、作為發行權子權利的提供權模式,也可以采用規定單獨的提供權模式(甚至可以用其它名稱)。
3.目的解釋方法
WCT序言第一句指出,締結WCT的目的之一,是因為“締約各方出于以盡可能有效和一致的方式發展和維護保護作者對其文學和藝術作品之權利的愿望。”這一措辭與《伯爾尼公約》序言第一句的規定基本一樣。“以盡可能有效的方式保護”是指“提供高水平的保護”。
另一方面,由于條約規定的只是最低保護標準,因此所謂的“一致”從邏輯上講,也暗含要求高水平的保護,因為最低保護標準越高,超過這個最低標準的空間就越有限,從而也就越容易獲得一致的保護。因此,在出現兩種以上可能的解釋時,應當采用有利于為作者提供更高水平保護的解釋方式。
4.補充性解釋方法
(1)“提供”的含義
(i)《伯爾尼公約》中的“提供”
“提供”(making available)一詞第一次出現在國際版權公約中,是《伯爾尼公約》1896年解釋性宣言對“已出版作品”進行定義時出現的。不過,直到1928年《伯爾尼公約》羅馬文本才將上述定義納入《伯爾尼公約》正文中:“已出版作品”一詞,在該公約中是指其復制品已經提供給了公眾的作品。
1948年布魯塞爾外交會議對上述“已出版作品”的定義進行了修改,后來,該定義一直維持至今:“已出版作品”一詞指得到作者同意后出版的作品,而不論其復制件的制作方式如何,只要從這部作品的性質來看,復制件的發行方式能滿足公眾的合理需要。盡管“提供”一詞從定義中被刪除了,不過,它仍然隱含地存在著。因為從定義的文本可以推論:“出版的”這一術語基本上還是指已經提供給了公眾的復制品,只不過現在的文本對復制品的數量施加了某些限制。當然,從邏輯來看,此種定義方式有很大缺點,因為其使用要定義的用語的一部分(已“出版”作品)來進行定義(“出版”)。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提供”這一用語在“已出版作品”的定義中出現時,其含義僅僅是指一種向公眾提供作品的可能方式,在中文文本中被翻譯成了“公之于眾”。
例如:《伯爾尼公約》第7條第(2)款:“但就電影作品而言……如自作品完成后50年尚未‘公之于眾’(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則自作品完成后50年期滿。”《伯爾尼公約》第10條第(1)款:“從一部合法‘公之于眾’(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的作品中摘出引文……就屬合法。”此外,還有《伯爾尼公約》第7條第(2)款、第10條之二第(2)款也使用了“公之于眾”(向公眾提供)這一用語。
在上述條款中,“公之于眾”(向公眾提供)這一表述沒有被加以任何限制,這表明:向公眾提供指任何形式的提供作品的行為,只要該“提供”的結果能夠使公眾中的成員可以獲得有關的作品即可。
此外,《伯爾尼公約》1967年斯德哥爾摩修訂會議的基礎提案所附帶的評論在提及“公之于眾”(向公眾提供)這一表述時,也明確地指出:公之于眾(向公眾提供)不僅僅限于出版,而且還包括第4條第(4)款[在《伯爾尼公約》巴黎文本中,是第3條第(3)款]第2句中規定的其它形式”。
(ii)WCT中的“提供”
考察締約歷史,我們發現,在確定選擇哪一些權利適用于數字網絡環境下的交互式傳輸時,締約各方意見不一致。時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負責版權事務的助理總干事米哈依?菲徹爾提出了“傘形解決方案”,并得到了各方的采納,從而為締結兩個公約鋪平了道路。
“傘形解決方案”的目的是提供一把“傘”(即多種選擇),使得權利人在數字環境下享有有效和充分的保護,同時便利各種不同制度之間的“兼容”。“傘形解決方案”的要件如下:
(a)應當將有關的行為表述為:向公眾提供;
(b)這種向公眾提供的行為應當包括:通過有線與無線方式或者通過有線與無線相結合的方式提供;
(c)這種向公眾提供的行為應當包括所有類型的提供,而不管其目的如何,也就是說:不管提供的目的是為了感知、研究、觀看、收聽以及/或者為了制作復制品;
(d)需要確認:無論公眾中的成員是在同一個地方同時接收,還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接收;也不管這些公眾中的成員僅僅是起一個被動接收的作用,還是有權決定他們什么時候獲得,都可以認為提供了作品或鄰接權客體;
(e)此種向公眾提供的權利的性質應當是專有權,而不能是獲得報酬權;
(f)應當根據上述提到的內容,消除現有的國際規范有關發行權和向公眾傳播權的規定所存在的漏洞。
在伯爾尼議定書委員會的準備工作的最后階段以及在外交會議上,大多數代表團都主張:在WCT中,應適用向公眾傳播權,因此上述對交互式傳輸所做的中立規定就被納入到了WCT第8條“向公眾傳播的權利”中。一些代表團將WCT第8條的這種規定,稱為“半開的傘”。
然而,美國代表團“強調,只要WCT和WPPT的有關條款所規定的行為,在締約各方的國內立法中屬于專有權的涵蓋范圍,則締約各方有權適用任何類型的專有權,當然也可以采用不同于向公眾傳播權和向公眾提供權的權利類型,或者將幾項專有權結合起來適用。
同時,WCT第6條規定了一般發行權,而《伯爾尼公約》對此沒有明確規定。WCT將發行權定義為:“授權通過銷售或其他所有權轉讓形式向公眾提供其作品原件和復制品的專有權”,其中也使用了“向公眾提供”這一措辭,也是為了回應一些國家代表團的要求,因為這些國家主張,應適用發行權來涵蓋交互式傳輸行為。
綜上所述,“提供”一詞的含義在WCT與《伯爾尼公約》一樣,都是指使作品處于可為公眾獲得/接觸的狀態,其范圍非常廣泛。既可以納入發行權,也可以作為向公眾傳播權的子權利,因此,才被作為“傘形解決方案”的核心要素而為各締約國所接受。
(2)公眾的含義
從公約的架構來看,可以認為被排除在“公眾”范圍之外的,應為“通常范圍內的家庭成員及其社會上的熟人”。WCT也沒有對“公眾”一詞予以定義,不過,WCT的措辭提供了一些更明確的指導意見:相關“公眾”是由“成員”組成,因此,“公眾”并不非得是眾多的;盡管可獲得作品的成員人數越多,就越容易得出結論,是向“公眾”提供。……即使提供的對象的范圍是受到限制的。
需要注意的是,WPPT的相關文件在就表演和錄音制品的提供權作出解釋時,對公眾一詞作了較為詳細的闡釋。這些文件認為“公眾”的含義包括以下特征:通常范圍內的家庭成員及其最密切的社會關系之外的群體;至于該群體是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時間還是在不同的地方和/或者不同的時間感知(保護客體)是無關緊要的。
如上所述,向公眾提供權是作為傘形解決方案的核心要素被納入WCT和WPPT的;盡管在WCT和WPPT中,向公眾提供權與向公眾傳播權的關系不同,但其自身的含義在兩個國際公約中是一樣的。
事實上,WIPO出版的《版權及相關權條約指南》也基本上采納了此種解釋:“公眾是指通常范圍內的家庭成員及其最密切的社會關系之外,由相當數量人數構成的群體。這一人群是否實際上聚在同一地點并不是決定性的,只要作品或相關權客體能被這一批人獲得即可。在向公眾傳播(包括廣播)以及(交互式)向公眾提供的情況下,能夠接收作品或相關權客體的公眾成員是否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接收也是無關緊要的。”
二、向公眾提供權的解釋與間接理論的提出
版權公約是以作者權為核心,締約目的也是為了給作者提供更高水平的版權保護,因此,在進行解釋時,應作出有利于作者的“擴張”解釋。不過,由于版權公約所使用的措辭本身可能就是非常寬泛的,因此,從文義解釋來看,作出有利于作者的解釋可能并不是“擴張”解釋。
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隨著衛星傳輸技術的出現,使得向公眾傳播權的架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關注的焦點是傳播形式是不是“向公眾”。與直播衛星不同,通過固定服務衛星傳輸的信號通常不能直接由公眾擁有的接收裝置直接接收,而需要先由地面接收站進行某種形式的“解密”,然后再將信號傳輸給公眾,或者通過有線或電纜進行分布式傳送。
有人認為,起源組織向衛星“發射”的信號不是“向公眾”傳播,而是“向地面接收站”傳播。當時,曾提出過一種解釋理論:即向公眾傳播既包括向公眾直接傳播:直播衛星直接傳播給公眾,也包括向公眾間接傳播:固定式服務衛星經由地面接收站傳播給公眾。
本文受到這一歷史的啟發,認為“向公眾提供權”包括向公眾直接提供(上傳至服務器的行為),也包括向公眾間接提供;在此基礎上提出間接提供理論,以規制深層鏈接行為。“提供”(making available)從字面意義來看,就是“使……可獲得”的意思,并沒有限制為僅可直接獲得;從條約目的來看,即使存在兩種以上的解釋,也應作出有利于為作者提供更高保護水平的解釋。
另外,本文提出的“間接提供理論”也可以得到“權威公法家學說”的理論支持。在國際版權公約領域,尤其是在《伯爾尼公約》/WCT領域具有權威解釋力的著作是山姆?里基森所著的《保護文學和藝術作品伯爾尼公約:1886–1986》以及他與簡?金斯伯格合著的前書修訂版:《國際版權與鄰接權——伯爾尼公約及公約以外的新發展》。
前一本著作在WTO審理的兩個涉及版權的案件中都為專家組所援引,即《美國版權法》第110條第(5)款案與中國影響知識產權保護和實施措施案;WTO到目前為止,審理的涉及版權議題的案件也只有這兩個。
后一本著作由于是在第一個案件發生后才出版的,因此,只在第二個案件中被援引。至于一些機構或者多位學者針對個案提交的意見或研究報告,諸如,對于Svensson案,歐洲版權協會(ECS)提交的意見以及國際文學和藝術聯合會(ALAI)與之相反的意見,并不能構成國際法意義下的權威公法家學說。
《國際版權與鄰接權——伯爾尼公約及公約以外的新發展》一書認為:
提供權可能還可以涵蓋某些間接地提供文學和藝術作品的行為,從而具有更廣泛的適用范圍……WCT第8條規定的提供權,授予了作者享有允許公眾中的成員“在其個人選定的地點和時間”獲得文學和藝術作品的專有權。“地點”一詞,最有可能是指公眾中的成員所處的地點(例如,家里或者網吧)。
不過,從第8條的文本來看,也可以認為“地點”一詞,是指網絡“地點”,例如,用戶為了獲得作品而訪問的網站……盡管傳播源最終是其它網站,但用戶的選擇才具有決定意義。如果是這樣,則WCT規定的“提供權”可以涵蓋某些間接侵權行為。
當然,為了互聯網的正常運行,采用“間接提供理論”,還需要配之以寬泛、靈活的權利例外制度。只要深層鏈接沒有與作品的正常利用相抵觸,也沒有不合理地損害權利的合法利益,則屬于例外的范圍,不構成侵權。
三、若干爭議問題之討論
(一)如何理解WCT第8條的議定聲明
關于WCT第8條的議定聲明的第一句規定如下:“不言而喻,僅僅為促成或進行傳播提供實物設施不致構成本條約或《伯爾尼公約》意義下的傳播。”
之所以在議定聲明中規定上述內容,是為了回應電信機構以及互聯網(接入)服務提供商的擔憂。他們希望確保其不致因其他人實施的侵犯向公眾傳播權的行為而承擔責任。不過,議定聲明的文本并沒有規定完全的責任豁免;而只是豁免了“僅僅為促成或進行傳播提供實物設施”的行為。
例如那些制造或銷售電纜、計算機或者其他從事WCT第8條中提供作品的行為所需要設備的行為。這表明,如果提供了實物設施以外的東西,如提供了可用于促成傳播的軟件,可能被視為是一種傳播行為。
至于WCT條款草案注釋所提及的“重要的是提供作品的初始行為;至于服務器空間、傳播連接(communication connections)、傳輸設備以及信號的路由選擇,則是無關緊要的。
”對于這里的“重要的是提供作品的初始行為”這句話,有觀點認為:“只有提供作品的初始行為”才能決定是否構成提供權意義下的提供。事實上,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只要存在提供作品的初始行為,即構成提供權意義下的提供。但并不意味著只有提供作品的初始行為,才可以構成提供權意義下的提供。
另外,草案注釋也只明確提及了四種”無關緊要的”情形,議定聲明也使用了“僅僅”一詞,因此應當嚴格解釋被排除在傳播之外的行為。
(二)如何看待歐盟法院的“新公眾”標準
由于《伯爾尼公約》和WCT都沒有對“公眾”一詞進行定義,但是,可否像歐洲法院那樣,采用“新公眾”標準?本文認為,這種解釋是值得商榷的。
歐洲法院最早是在SGAE訴Rafel Hotels案中,引入“新公眾”標準的。歐洲法院認為,根據《伯爾尼公約》第11條之二第(1)款第(ii)目的規定,該案中發生的傳播行為,屬于由原廣播機構以外的另一機構進行的傳播。因此,此種傳播的對象是向不同于原始傳播行為所針對的公眾以外的其他公眾,即“新公眾”。
正如《伯爾尼公約指南》所解釋的那樣……當作者授權廣播其作品時,他所考慮到的只有直接使用者,即那些擁有接收設備,單獨或者在其私人或家庭圈子內接收節目的人。根據該指南,如果接收是為了令更多的人,即新的接收公眾收聽或收看作品,可能是為了利益,則通過擴音器或類似工具傳播節目,不再構成簡單的接收節目本身,而是構成向新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的獨立行為。
事實上,此種對《伯爾尼公約》第11條之二第(1)款第(ii)目和第(iii)目的解釋是錯誤的。《伯爾尼公約》第11條之二第(1)款包括以下內容:“(i)授權廣播其作品或以任何其他無線傳送符號、聲音或圖象的方法向公眾傳播其作品;(ii)授權由原廣播機構以外的另一機構通過有線傳播或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iii)授權通過擴音器或其他任何傳送符號、聲音或圖象的類似工具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上述第(ii)目所規定的權利,并不要求向“新公眾”傳播。
歐洲法院之所以作出錯誤解釋,可能是錯誤地依據了舊版的《伯爾尼公約指南》進行的推理;此外,它也錯誤地理解了《伯爾尼公約》第11條之二第1款第(iii)目,該條款其實規定的是公開表演權,而并非“向公眾傳播權”:這一點從WCT第8條中的“不損害”條款未提及它可以得到證明。
《伯爾尼公約指南》對《伯爾尼公約》第11條之二第1款第(iii)目進行解釋時,作了如下說明:“正如在通過電纜傳送廣播電視節目的情況下,有額外的聽眾或觀眾產生(第1款第(ii)目)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也使作者在他授予許可時未曾預料到的聽眾(和可能有的公眾)感知到該作品。”需要指出的是,該《伯爾尼公約》指南是1978年出版的;新版指南并不采取這一觀點。
廣播權最早出現在1928年羅馬文本中,當時只有一項內容,即“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權通過無線電發送(radio-diffusion)向公眾傳播其作品的專有權利。”之所以作如此安排,有多種技術方面的原因;不過,通常的原因是因為地勢、人為造成的地理結構、距離以及時差。
例如,由于一個地方地處山區或者被高層建筑物所阻擋,原始的廣播信號可能就很難到達此地。又比如,在一些幅員遼闊的國家,遠距離傳輸廣播信號,可能需要中轉站進行一次新的傳輸,以“加強”信號,以便原始的廣播信號能夠到達遙遠的社區。
上述情形所引發的問題是,對原始廣播進行后續的傳輸是否應被視為新的廣播行為,還是應被視為屬于原始廣播的范疇。在1948年布魯塞爾外交會議上,外交會議預案建議應授予文學和藝術作品的作者一項新的權利:即“任何新的以有線或無線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的權利”(any new communication to the public, whether by wire or not, of the broadcast of the work)。
根據備忘錄的解釋,上述草案條款的含義是指,任何針對新的聽眾群或觀眾群的廣播,無論是通過新的無線發射還是有線傳輸,都應視為是一種新的廣播行為,應得到作者的專門授權。事實上,要區分原始聽眾與新聽眾,在理論上比較容易,在實際操作中就比較困難了。
最終,1948年布魯塞爾文本采取了現實的解決方案,即規定“由原廣播機構以外的另一機構”通過有線傳播或轉播的方式向公眾傳播廣播的作品,才需要獲得作者的單獨授權。
因此,在《伯爾尼公約》第11條之二第1款第(ii)目的架構下,是由于出現了新的傳播主體,而非出現了新的傳播對象(公眾),所以需要獲得作者另外授權。綜上所述,“新公眾”標準盡管作為建議被提出過,但最終條約正式文本并沒有采納,條約文本采納的是“新(廣播)機構”標準。
在考察了《伯爾尼公約》第11條之二第(1)款的發展歷史之后,再來看歐洲法院在SGAE訴Rafel Hotels案的判決,就會發現,歐洲法院其實誤解了《伯爾尼公約》的含義,從而錯誤地在該案中引入了“新公眾”標準。
四、結 論
每一次技術發展都會對版權法制度提出挑戰,從而要求版權法制度對其作出回應。網絡深層鏈接就是這樣一種技術。當然,版權法回應的方式,可以是采用“新的規則”,也可以是采用“澄清對某些現有規則的解釋”。不過,一般而言,如果采用法律解釋的方式能夠解決問題,最好還是不要采用創設新的規則的方式。
作為WCT的成員方,歐盟《信息社會版權指令》第3條與WCT第8條規定幾乎完全一樣;而且當年外交會議在WCT中規定第8條,也是采納了歐共體的提案。歐盟法院就涉及《信息社會指令》第3條的解釋,對于我們理解WCT第8條意義下的“向公眾傳播權”、“向公眾提供權”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
然而,歐盟法院在早期審理的案件中,錯誤地引入了“新公眾標準”,近幾年,一直在試圖糾偏。這也說明,有關“向公眾提供權”、“向公眾傳播權”的含義問題、深層鏈接的性質問題,在歐盟層面還處于探索結論,尚未形成定論。
至于我國,這幾年對涉及網絡深層鏈接問題的實踐與理論也有很大爭議。從早期的“服務器標準”與“用戶感知標準”,到近來“實質呈現標準”的提出,都不斷豐富了相關領域的理論。然而,正如歐盟一樣,對于這一問題,在我國并不存在“理論的終結”,還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 商標查詢
- 版權查詢
便捷鏈接: 商標查詢 商標注冊 版權登記 專利申請 海外商標注冊 商標交易
本文來源:中國商標網 - 論世界版權公約中“向公眾提供權”的含義
版權說明:上述為轉載或編者觀點,不代表一品知識產權意見,不承當任何法律責任






















